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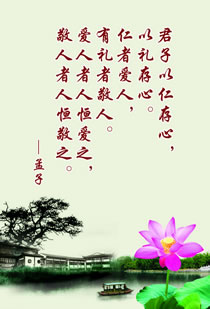
《孟子》一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以其独特的“文学性”闻名于世。其文辞华美、流畅自如,气势恢宏,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自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心驰神往,倾注毕生心血去研读、诠释、传承。
“三苏”父子中,苏洵对《孟子》的评价极高,他认为孟子的文辞简约而意蕴深远,虽无尖锐刻薄之言,但其犀利之处却令人难以抵挡。苏轼、苏辙兄弟深受父亲影响,自幼便研读《孟子》,苏轼更称孟子深谙《诗》与《春秋》之道,且自谓学识源于孟子。梅尧臣作为考官,曾赞赏苏轼的应试作品《刑赏忠厚之至论》颇似《孟子》之文。
汉代赵岐则指出,《孟子》擅长运用比喻,其言辞虽不迫切,但意蕴深远。现代作家鲁迅认为,孟子生活在周季,其文辞逐渐繁复,但叙述之妙却令人叹服。郑振铎亦评孟文辞意骏利、比喻赡美。钱基博更称,《孟子》为儒家之文中的佼佼者,其文跌宕顿挫之妙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孟子》还广受世界范围内的赞誉与传播。在汉字文化圈的韩国、日本、越南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孟子》备受推崇。同时,它也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牛津大学更是将《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则将其列为古文教本,进一步推动了孟子思想在西方的发展。从18世纪开始,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便深受孟子思想启发,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
不仅如此,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也深受《孟子》的影响。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读到孟子见梁惠王的“义利之辨”时,曾深感震撼并发出感叹。此外,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孟子的生平事迹及其游历各国的经历。
与孔子相似,孟子亦游历于各诸侯国,致力于宣扬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理念。他不仅在《列传》中提及的齐、魏(梁惠王)等国留下了足迹,更曾踏入宋国,经过薛地,回到邹国,再到鲁国,甚至会见过齐威王、宋康王、滕文公、邹穆公、鲁平公、梁襄王等多位君主,这一过程历时二十余年。那时,战国中期正值各国诸侯争霸之际,他们皆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与军事的强大,企图通过战争来统治天下。然而,孟子却坚守着唐、虞、三代之德的信仰,他的理念在当时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因而与当时的潮流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孟子并未放弃,他转而与万章等人一起整理《诗》《书》,阐述孔子的思想,最终著成了《孟子》七篇。
这篇传记虽然近两千字,但关于孟子的描述却仅占不到两百字。接下来,文章将转向先秦诸子之一的驺衍,对他的描绘将占据几乎三倍于孟子的篇幅。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将邹衍在齐、魏、燕等国所受到的尊崇、厚待与孟子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梁惠王准备出兵侵略赵国时,他向孟子请教。孟子则引述了周代先祖古公亶父在面临戎狄侵略时的故事,讲述了他如何不忍杀戮、离乡背井的抉择。司马迁对此感慨道:“这哪里仅仅是迎合世俗罢了!他手持方榫却要嵌入圆孔,这可能吗?”“有人说,伊尹因为负鼎而辅佐商汤称王,百里奚因饭牛而助秦缪公霸业,他们都是先有所合而后引领大道。驺衍的言论虽然离奇,但或许也蕴含着类似的深意吧?”司马迁将伊尹、百里奚与驺衍的做法与孟子的行事并置,供读者评说。
孟子不愿“迎合世俗”,他真的如梁惠王所称的“迂阔”之人吗?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孟子,我们有必要再从《孟子》一书出发。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他出生在孔子之后一百余年,三岁便失去了父亲,由母亲仉氏独自抚养长大。东汉时期的学者赵岐在《孟子章句·题辞》中称赞孟子幼时便受到了母亲的深刻教导。
《列传》中记载,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子思正是孔子之孙孔伋。孟子虽未能亲受孔子之教,却深感遗憾,他私心仰慕,自视为学生。孟子毕生景仰孔子,曾言:“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孔子。”他由衷地赞叹道:“自有人类以来,未曾有过孔子这样的圣人。”
在孟子“道既通”后,他仿效孔子,在家乡设馆收徒,教书育人长达十余年,致力于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三大乐事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成为“天子”。
孟子44岁时,他效仿孔子,肩负着“木铎”的使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期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推行仁政,重振王道。然而,他耗费了四分之一的生命,终究未能如愿。最后,孟子回到家乡,继续讲学育人,著书立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孟子的一生都紧紧追随孔子的脚步,致力于成为“亚圣”。
尽管孟子与孔子的性情、气质有所不同,但他们在事业上的追求却高度一致。孔子以温柔敦厚、谦谦君子之姿著称,《论语》中偶尔流露出因理想不得实现而产生的情绪波动。而孟子则显得更加“英气勃勃”,他的自信与豪情在游说权贵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孟子曾言:“游说权贵时,应藐视其巍峨之势。”他接着豪迈地宣称:“即使宫殿高耸、排场宏大,我也不会为之所动;美食佳肴、侍妾成群,更不会令我迷乱;纵情声色、车马驰骋,也不会让我沉溺。我所追求的,都是古圣先贤的遗训。”这番言论彰显了孟子的坚定信念与豪迈情怀。
孟子强调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从不屈服或迎合权势。当朋友景丑氏批评他对齐宣王不够尊敬时,孟子回应道:“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爵位、年龄和德行。在朝廷上,爵位是最尊贵的;在乡野里,年龄则最为尊贵;而辅佐君王、治理百姓,德行无疑是最尊贵的。怎能因其中之一而轻视其余呢?”他还提出,那些主动迎合、顺从权势的公孙衍和张仪,所行的是“妾妇之道”,与他的理念相悖。
正因孟子这种“泰山岩岩”之气象,他在《孟子》中首次提出了“大丈夫”的概念。他阐述道:“住在大路之上,立身在天下最正直的位置,行走在天下最大的道路。得志时,与民共享;不得志时,独自坚守正道。富贵不能迷乱其心,贫贱不能改变其志,威武不能屈服其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理念,回答齐国王子垫的问题时说:“居住在仁的怀抱中,遵循着义的指引,这就是大人应该做的事情。”他还提出:“真正的君子,言不必信守每一句,行不必坚持每一事,只要合乎道义即可。”
此外,孟子还强调了“养志”与“养气”的重要性。他认为,“志”与“气”相互影响,“我善于培养我自己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充沛旺盛,无法阻挡”。他进一步提出,“仁者无敌于天下”,即有仁德的人在天下无敌。
我们耳熟能详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强调了“动心忍性”的重要性,而这关键在于“志”。没有坚定的志向,即便是“劳其筋骨”也难以有所成就。
孟子所倡导的“居仁由义”、立志“养志”、培养“浩然之气”,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定立场,共同塑造了一个“大丈夫”的形象。这一形象不仅是对孟子本人的写照,更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处世的高标准。千百年来,“大丈夫”一词被士人反复引用,深入人心。
从东汉的太史慈到明代的张居正,再到唐代的杜甫,无数志士仁人以“大丈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孟子所强调的“人性本善”与“养大体为大人”的理念,指引着人们沿着《孟子》的道路前行,追求成为真正的“大丈夫”。
孟子胸怀壮志,立志于“平治天下”。他豪言壮语地宣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种气魄与担当,正是“大丈夫”精神的体现。
同时,孟子还提出了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以仁爱之心,不顾君王感受,屡次直言进谏,为民请命。这种以民为本的立场,无疑是对“大丈夫”精神的进一步升华。
在《孟子》的结语部分,孟子回顾了自尧、舜至汤的五百余年历史,并与前文《公孙丑下》中提到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舍我其谁也”的观点相呼应。他感慨道,像禹、皋陶这样的圣贤,他们是亲眼见证并传承了圣人之道;而汤,则是通过听闻来领悟并实践了圣人之道。然而,自孔子时代至今,虽已过去百余年,却似乎仍未能有人能真正继承圣人的大道。孟子不禁发问:“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种对未能继承圣人之道、实现自己理想的深切遗憾,读来令人动容。
此外,孟子还展现了他“雄辩、弘毅、自信”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善讽喻、善幽默”的智慧。这些丰富的性格特点,都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孟子》以及孟子的宝贵视角。
读《孟子》,不仅是一次智慧的旅程,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只有深入学习和实践孟子的思想,才能真正体会到他那种追求真理、坚守道义的精神。因此,学做孟子,或许是我们纪念孟子、传承其思想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