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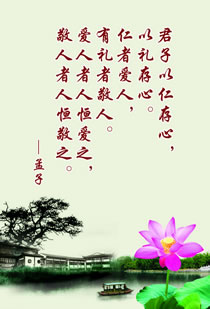
近来看了军旅书法家、省书协主席孟世强先生新近创作的多幅作品,又回过头与他在六年前出版的《孟世强书画集》里所收的作品粗略对照了一下,发现作为书法家的孟世强先生,在求索书艺不断精进的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各种突破自我、丰富笔墨表现内蕴等方面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和探索。
从习书经历和书法资源的层面上看,孟世强“八岁随父习字,数十年来从未间断。楷书临习过欧体、魏碑、颜体;隶书临习过石鼓文、汉简,行草书临习过二王、米芾、何绍基等体。”这句话所蕴藏的信息,至少说明孟世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的,各种书体的实践,使他对书法的渊源脉络了然于心,也使他的书风呈现出诸美兼容的特点。大凡在历史上出现的书法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创作规律:真草隶篆诸书体间相互渗透、交融,常常诸体互用互通,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而且诸体间的杂糅也在无形中提升了书法创作的门槛,增添了书学修养对作品神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悟性和才气,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对多种书体所具有的美感元素的巧妙结合。
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书法史上出现的重要书体———篆书、隶书、楷书均有研修。这种研修,尤其是来自汉碑隶书的那种勃然生发的古朴气象,与他天性中的某些精神需求、趣味、嗜好完全契合。他的隶书,在气势上追求开张的效果,如表现出线条的《张黑女》、《石门颂》圆润劲健的笔意———平直中隐隐带着起伏、波荡之势,不求略带弧线的俊朗之美,而是刻意追求方刚劲拔的朴拙昂奋之美。篆书取小篆之体,圆润中更多地带着浑厚的气韵;楷书基本上以颜体书风为基调,流动恣意处每每带出二王、米芾、何绍基诸家的笔意。孟世强近期的书法风格和前期相比,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首先从书写内容上,由过去的古诗、短句更多地转向了书论的书写,这至少可以暗示出他在书法创作层面上具有相当自觉的理性修养和眼光;其次是结体、笔法、章法有所调整,先前被着意强化的走笔的滞涩感、纤细的线条、拉长的字体,一变而为浑圆朴茂、厚实流畅的线条;字体变得更为结实、绵密;章法上不仅保持了原有行距的宽舒,而且行与行之间加强了字体大小的对比度,错落有致。
与飞逸恣肆的书风相比,孟世强的笔墨线条不似急速扯动的丝帛———飘逸、轻盈,过于闪烁不定,他在骨子里更愿意致力于让笔墨线条具有沉重感和密度,以便显现出大山般的沉稳,颇有艺术家熊秉明评价伊秉绶的字那样“给人以宗庙殿堂的建筑感”。这样的灵感和感悟,一定得益于他对颜字的感悟。可以说,孟世强书风中表现出的沉重感和密度,大半来自于颜体的丰腴、宽博、浑厚。
这样说并不是说孟世强就排斥轻盈感,而是说他不满足于单纯的轻盈感,不满足于单纯的美感,他至少要在两种相互对立、补充的美感中去寻求内在的张力。所以他笔下的轻盈一定会带着沉重,他用笔的节奏也会相应地变得缓慢。在遒媚典丽和丑怪的两路书风里,他既不因为企慕遒媚而流于妍秀,也不因为追求字形的多姿多态而失之狂野、畸怪。我以为他的书写激情总是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张力,似乎时时保持着一种书卷情趣、兴味和自然的松弛心境与走笔的法度之间相互不断的调试。
孟世强前期的书法风格,确实充盈着一种飘逸的风采,但这种飘逸不时地被一种苍拙之气笼罩着,以至于那些舞动的线条在行进当中随时都在扭曲、颤动和摇曳,随时都呈现出被时光流年剥蚀出的那么一种苍老、陈旧的气息,婀娜健朗有如古树老枝。他写的李白诗,正是这种书法风格的写照。近期之作,大大地减少了用笔的提按顿挫,先前线条的扭曲、颤动代之以现在的迅捷流畅,笔画吸收了章草、草书的简洁之美,笔墨酣稳、饱满,大量融合了篆隶的笔意。
下面我就尝试着说说他的几件最近的作品。
第一件是他的行书条幅———高骈《山亭夏日》诗:“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诗歌的意境重在表现恬静安谧,微风和花香的神韵在于轻盈、朦胧,书写的时候就着意以枯笔来表达微风和蔷薇花香的轻盈、虚幻、空明和清淡。孟世强的书法,笔画的牵丝连带很少,字距和行距都显得极为宽展,字的转角用笔多圆转,有颜柳的沉着。像“入池塘水晶”、“一院香”诸字,笔墨看似用尽,但还是一笔写定,运笔清晰,其笔法让人想起米芾《虹县诗》卷中“一天清洲”的笔法。这种用笔难度颇大,以中锋为主,既要让墨留在纸上,又不能使笔毫散开。尤其是“池塘”二字,节节加劲,转折处用笔严谨不显松散;“池”字的收笔没有按照通常一拉到底、以尽其势,而是笔画有意从半中腰断开,意态上像硬钢崩裂,蓄其势。“动”字周围,乍看整体形成极富视觉冲击感的墨块,细瞧,“动”字的最末一笔和“微”字的起笔都用渴笔,使之与重墨书写的“楼台”、“帘”诸字形成浓淡的关系对比,所形成的空间,如同围棋中的高手放一子便可以救活一角。
第二件是他的一件小型的行书横幅。此件作品书写的是刘禹锡的《杨柳枝》。其中起首的“清”字的偏旁点画方圆相互映照,右边的“青”字颇具篆隶笔意。“一曲”两个字间的距离被大大地压缩,与上下连接的字形成灵动自如的疏密关系。“二十年前旧板桥”一行,既有二王遗韵,又有颜体风采。“曾与美人桥上别”中的“桥”字的偏旁点画,稚拙朴野,酷似《居延汉简》中的某些笔意。诗中大多数的横折笔画圆劲茂美,既有篆书的圆实,又有颜体的酣稳。
行书横幅《古人论书句》,结字优雅,用笔清健,书写的速度较快,因而出现了多处牵丝,这是气韵连贯、技艺娴熟方能制造的效果,从中颇能窥得文中所言的“小字亦具飞动之势”的美感。
扇面书法《虚怀若谷》,具有榜书的气势,结体简劲,前两字以圆笔为主,圆转遒美;后两字侧重于方笔,棱角犀利,最后的收笔蕴藉中仿佛包含着千钧之力。整个作品的气韵,既有汉碑雄肆之气,亦有化古为我、焕然一新的气象。
在解读、赏析孟世强的书法艺术时,我们还应当留意他在中国画创作上的造诣。他的绘画总体上也是与他的书道一样,偏爱营造浑厚淋漓的墨彩意境,格调上完全承接文人画家高雅俊逸的气息、脉络,无论是画梅时的分枝布叶,还是墨彩淋漓的山水、水乡、花鸟,都点染得苍润浑厚,没有半点媚俗之气。这样的杂取旁收、厚积薄发,不仅使他的书画艺术具有一般单纯从事书画的人所不具备的韵致,而且更为他将来取得更高的艺术造诣,埋下了令人期待的伏笔。(作者:马钧)
